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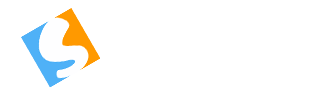
国庆档的院线里,10月4日中途上映的《震耳欲聋》是个“异类”。
没有飞天遁地的特效,没有博人眼球的话题,它讲的是一群“沉默的人”——聋人群体遭遇诈骗,以及一个夹在“两个世界”之间的律师,如何为他们发声。

《震耳欲聋》海报
导演万力第一次见到张琪律师时,对方正在处理一起聋人房产诈骗案:一位大叔下班回家,发现门锁被换,屋里住了陌生人,掏出的房产证早已易主。他张着嘴想辩解,却发不出能被“听见”的声音,最后只能揣着空荡荡的口袋,连夜找地方落脚。后来她又遇到一个女孩,母亲遭遇金融诈骗后房子被收走,一家人颠沛流离多年,直到怀孕生子,才敢说“好像走出阴影了”。
而这个成长在聋人家庭的CODA(指聋人父母的健听子女)律师,为弱势群体打官司也不是理所当然的生长正义,也有自己想要挣脱泥沼的身不由己。
这些真实的疼痛,成了《震耳欲聋》的起点。它没把“聋人反诈”做成猎奇的社会新闻,也没把律师拍成无所不能的英雄 —— 它只是老老实实讲了一群普通人的挣扎:有人丢了房子,有人丢了身份,有人在利益和良知间反复横跳,最后却都选择“自己站出来”。
10月4日,由饶晓志监制、万力导演,檀健次、兰西雅、王戈领衔主演,王砚辉、迟蓬特邀主演,潘斌龙特别主演的犯罪剧情片电影《震耳欲聋》上映。澎湃新闻记者和监制导演,聊了聊这一次,他们如何去听见那些“无名之辈”发出的声音。
聋人并非博取同情的符号
在传统的影视作品里,律师常常是功能性的,非黑即白的角色,要么大义凛然地伸张正义,要么成为利益集团的帮凶助纣为虐。而电影中的李淇是一个游走在黑白间的“灰度律师”。他出身于底层,对于名利的追逐是毫不掩饰的赤裸。他会对弱势群体开出“2000一小时”的明码标价,并直言打消对方“道德绑架”的念头,对于“吃力不讨好”的案子敬而远之,甚至为了连带利益对眼皮子底下的不公不义选择性无视。他成为“聋人群体”代言人,享受公益光环带来的便利,懂得利用大众的同情心以此作为自己事业晋升的标签;他接受社会的规则是“弱肉强食”,但也会被同伴一次次质问的“公平与正义”激荡起内心从未泯灭的正义感。

檀健次饰演的“灰度律师”李淇
张琪的经历本身就充满戏剧性:小时候回家用手语和父母沟通,聋人群体觉得“你会说话,该帮我们翻译”;在学校里,同学又觉得“你是聋人家里的,和我们不一样”。这种“两头不靠”的身份困惑,成了李淇角色的底色。
万力在采访里特意提到,正是原型人物成长经历中的那些挣扎,让他看到创作中潜藏的巨大空间。他不想做“完美英雄”:“每个人都有对身份怀疑的时候,也都有对金钱、名利的渴望,但也都有善良和正义的底色。”

导演万力
拍特殊群体,“美化”或“猎奇”在影视剧中也总是常见的。 要么把他们塑造成纯粹的受害者,要么放大他们的“特殊性”,变成供人同情的符号。但《震耳欲聋》没这么做。
万力和团队做了三个月调研,采访大量聋人群体。他发现,现实生活中,特殊群体会自然组成自己的社区。电影里的“玩具厂大院”,就取材于张琪妈妈曾在工作的玩具厂大院。院里有修轮胎的老马(潘斌龙 饰),有打麻将的阿姨,有晒被子的老人 —— 这些细节都来自张琪的回忆:“他小时候有对聋人邻居修自行车,每次见他都特别开心,拉着他去吃饺子。”万力把这个细节放进电影,张琪在第一次看电影时就忍不住泪流满面。
更难得的是,电影没回避聋人群体里的“复杂”。王砚辉饰演的反派,本身也出身于聋人家庭,却利用聋人之间的信任诈骗房产;兰西雅饰演的角色,也会教小孩用“同情牌”骗钱。饶晓志在采访里直言:“我们没打算美化谁,弱势群体也有贪恋,也会犯错——因为他们首先是‘人’,不是‘弱势群体符号’,而我们做的,是去‘直面’他们。”

影片中同样身为CODA的反派,由王砚辉饰演
拍摄时,剧组请了12位真实聋人演员,这也给主创出了难题。一开始需要手语老师翻译,但慢慢地,现场工作人员都学会了简单手语。万力记得有次拍完戏,她用手语说“大家演得好”,聋人演员也会用手机打字跟他聊角色。
最让执行制片人难忘的是一次“角色互换”:手语老师临时不在,他要跟聋人演员沟通拍戏细节,只能靠手机打字。“那时候才发现,我成了‘少数群体’——他们打字比我快,沟通比我顺畅,我却因为看不懂手语,急得满头汗。”万力说,作为“听人”,他们也突然感受到了那种沟通的障碍,和不被理解的窘迫,“很多这样的时刻都帮助我们更加理解他们的感受。”

监制 饶晓志
监制饶晓志把这种状态总结为“普通人的成长路线”:“很多人都在试图逃离自己的原生家庭的影响,我自己也一度非常想要逃离我自己的县城和小镇。”在饶晓志看来,自己身边也有做律师的人,除了在律政剧里的舌战群雄,大部分时候他们面对的也是繁琐的工作,也会有自己对职业晋升的苦恼。李淇的“灰度”,是人之常情的趋利避害。“哪有人生下来就充满正义感?从小他成长在这样一个群体,就注定了天然要为它发声。”饶晓志说,“我们做这个片子,就是想破除过往很多作品对这个人群脸谱化的塑造。无论是CODA律师也好,聋人群体也好,他们就是我们的正常人,也有他们自己的难题。”
声音设计不炫技,只让观众“走进”沉默
作为一部讲“聋人”的电影,声音的处理成为不亚于视觉表现的重要手段。《震耳欲聋》在这方面做得更用心,但也十分克制。
影片从开场出现出品方字幕的时候,就开始用声音营造一个不同于常规听觉空间的世界。创作者对于不同程度听力障碍者所感受到的声音和振动感做了模拟,让走进影院的观众能够在第一时间产生直接的感官体验。

《震耳欲聋》 剧照
还有电影里的 “耳鸣音效”—— 不是尖锐的噪音,而是低沉的振动,像有什么东西堵在耳朵里。万力说,这种音效是专门为影院设计的:“只有在电影院,你才能感受到那种从座椅传来的振动,像聋人朋友说的‘听不见,但能感觉到’。” 当然,这种感官感受是否真的接近于聋人群体的体验和处境,身为听人的导演其实无法证实或证伪,“听觉体验是主观的,他们只能通过手语或者文字描述,而我们能够做的只是让观众沉浸地去感受。”

玩具厂大院里的老马
电影在声音设计上的心思,不光体现在模拟物理上的感官刻画,还有许多对于生活化场景的营造里也藏着创作者的用心。比如李淇第一次走进玩具厂大院的戏,声音设计做了个 “反套路” 处理:有打麻将的哗啦声,有炒菜的滋啦声,有晒被子的风吹声——但没有任何人声。“你站在李淇的视角,就会明白:聋人的世界不是‘静音’,而是‘少了一种声音’。”
而电影中的台词,也由于手语的加入,变得拥有了更大的品评和读解空间。影片上映后,有懂得手语的网友解读出,片中演员比画的手语其实比字幕直译出的信息要更加丰富,情绪也更加强烈。对此,万力解释,手语,是另一套语言系统,包含了表情和肢体两部分——“两个聋人交流,戴上口罩可能就理解不清对方的意思”。“就像微信聊天要加表情包,”万力打了个比方,“同样一句‘没事’,配上微笑表情和皱眉表情,意思完全不一样。手语的表情,就是聋人的‘表情包’,是他们的情绪出口。”
国庆档里的现实主义:给普通人的勇气
2025年的国庆档依然热闹,《震耳欲聋》在国庆假期的中段上映,像一块沉默而坚毅的石头投入奔涌的河流,以稳健的现实主义姿态,补上了一块属于“无名之辈”的拼图。
这是监制饶晓志又一次将目光对准社会边缘的小人物,他对记者谈起自己对“小人物”的偏爱。“我一直拍小人物,无论是《无名之辈》还是《震耳欲聋》,都是自己生而为人的一些期许,是一种对美好的期许。这也算是我作为创作者的一种思考和创造力的角度。我们大部分人有乏味的时候,这时我们究竟要站在哪一方,做出什么样的选择,这是这样的人物能带给我们力量的地方。”

《震耳欲聋》海报
对于已经“征战”过包括春节档、国庆档等各个主流大档期,也凭借《万里归途》拿下三年前国庆档冠军的饶晓志而言,这次选择国庆档一方面是希望这部电影能给观众“不一样的现实主义关切”,“通过人物的成长来把普通人的这种心声讲出来”,另一方面,饶晓志也对电影作为一部符合商业类型片叙事的好看程度有信心。
“虽然是现实主义,但其实我们还是把它当作一个类型片去创作。”导演万力并不希望观众到影院来“吃苦”,谈到影片最初的定位,就是希望能拍一个“好看的,甚至是娱乐性的影片”。“其实当下大家生活中都有很多不容易的事情,我们还是希望能够给观众一个很好的体验。体验之余,还能够有一些感动,那是锦上添花的事情。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鸡蛋”,饶晓志在采访中调侃道。过去长辈们可能栽在“领鸡蛋”的陷阱里,聋人群体却因信息壁垒、沟通障碍,成了诈骗分子瞄准的目标,而现实生活中,不同生活文化背景的人,也似乎会在各种层出不穷的手段中遭遇花样百出的诈骗。万力导演跟随张琪律师采风时,他才知道被诈骗的人远比他以为的要多得多。

电影海报
“很多人出于面子,或是觉得‘申诉无门’,连被骗的事都不愿提起,可那些伤害会变成一辈子的阴影。”而拍摄这样一部电影,一方面是想让大家提高警惕,另一方面,更想让观众明白,面对困境,需要主动“发声”。
“我们电影的主题,就是要‘发声’,要自己做自己的英雄。很多时候在你遇到困难无助的时候,可能会有人来帮助你。但是可能大部分情况还是需要你自己有勇气站出来,虽然我们展现的是一群所谓的特殊群体,但我也希望是能够让每个人都有共情。”
这是一条公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