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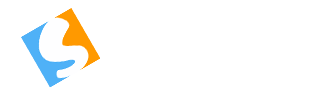

与电视剧《北上》主要聚焦90后青春、爱情、成长和奋斗不同的是,徐则臣的小说“阔大开展,气韵沉雄”,以大运河边几个家族之间的百年秘史和颠沛命途揭示千年长河的兴衰命运,横跨历史与当代、朝野与官民、南北中国与东西世界。
一些通过剧版《北上》才知道徐则臣的观众,看过小说后惊觉:差点错过近几十年中国最重要的作家之一。而不少原著党对电视剧几乎脱离原著讲述故事颇有微词,徐则臣对此却态度随和:“我没什么意见,改编是让小说继续成长。”
“为人须谦和平易,作文要一意孤行。”这是徐则臣在最近再版的自选集序言中的一句话。写作之外,他随和,沉稳,低调,有着“水系” 的性情。
早年间,徐则臣从北大中文系硕士毕业到《人民文学》做编辑,不久就推出了作家龙一的现象级作品《潜伏》,如此才有了国产爆款谍战剧最经典的潜伏者——余则成。某种程度上,徐则臣就是余则成的 “原型”。龙一觉得他的名字很适合搞地下工作,便去掉“徐”的双人旁,改“则臣”为“则成”以寓意成功,主人公余则成诞生。
而幕后功臣徐则臣一直“潜伏”在北京,醉心创作。40岁之前写出了《如果大雪封门》《跑步穿过中关村》《耶路撒冷》《王城如海》《北上》等数部代表作,获得包括茅盾文学奖在内的数个顶级文学大奖的认可,身上还被“焊”上了诸如“70后作家的荣光”等标签。
今年2月,徐则臣在《人民文学》工作整整20年后,升任这本中国文学王牌刊物的新晋掌门人,成为继茅盾、张天翼、王蒙、刘心武等人之后第15位主编,首位70后主编。
与徐则臣的见面过程非常顺畅,没有预想中的通报、等待,走过一条挂满了在《人民文学》上发表过、提到中国文学必然不会绕过的名家名篇史料档案镜框的走廊,便看到身着轻便卫衣牛仔裤运动鞋的徐则臣,微笑着站在门口迎接。
看得出他刚搬到这间十来平米的办公室。桌边、地上都堆满了书籍报刊杂志,以及装满书的纸箱、包裹。办公桌对面一整面墙都是书柜,旁边还有一个立式旋转书柜。这让整间办公室略显局促,也简朴至极,除了沙发边一盆半人高的龟背竹,没有其他装饰,连饮水机都不见,泡茶用的是久违的热水壶。若不是办公室门上贴着“主编”的铭牌,你很难意识到,对面坐着的是当下中国文坛举足轻重的领军人物。
访谈中,时不时会有人推门进来,请示编务、行政、人事、差旅等事宜。他总是先聆听对方的意见,再有商有量地给出自己的想法,平和、实在、没架子。
原本不用坐班的他,自2018年上任副主编之后,就如一个朝九晚五的上班族那样,只要不出差就在办公室处理工作。被他视为生命的文学创作,目前也放在了第二位,只能利用节假日来闭关写作。工作事务日渐繁杂,他已经很长时间没有正经写小说了。关于“运河”系列,《北上》之后,他还有一部长篇小说,以及若干短中篇的写作计划,但进展缓慢。原因无他,只因“现在的纸媒和纯文学都非常式微”,这是他甫一上任就面临的困境。
十年前,徐则臣在上海做演讲时提到,“正因为零距离地置身急剧变化的世界,零距离地置身当下文学现场,文学对新一代写作者有了另外一个难度:如何及物地表达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真实感受和想法?”
十年后,当他成为《人民文学》新主编,要带领这本与共和国同龄的新中国第一本全国性文学刊物,去面对剧变的世界时,他当年强调的突破创新,已经从口头笔尖到必须躬身入局。


黑色条纹西装/Issey Miyake
格纹T恤/Giorgio Armani
去年,徐则臣和同事们做了一件事,他认为应该将之写入中国传统文学刊物发展史——《人民文学》走入董宇辉的“与辉同行”直播间,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开展杂志宣传和订阅。
两次直播,第一次在4个小时内获得上亿次点赞,达成近百万册订阅量,成交金额达1785万;第二次,两小时吸引700万观众,最高在线人数达27.8万,再次达成近30万册订阅,成交金额近500万。
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突破性订阅数据。由此也引来非议:文学不应该这样放下身段委曲求全;纯文学要坚守“文学纯粹性”;文学国刊怎能向世俗低头……4月19日,“人民文学奖”把“传播贡献奖”颁给董宇辉,更让争议登上热搜。
徐则臣此刻淡定地置身风口浪尖之外。在此之前,他已经长久地伫立在各种水流的交汇碰撞之处了。
2005年从北京大学中文系硕士毕业,徐则臣就到《人民文学》杂志做编辑,20年没有挪窝,是全社工龄最长的人,完整经历了传统文学期刊“从还算招人疼惹人爱到越来越遇冷、越来越边缘”的全过程。这边缘化的程度,甚至到了令人惊惧的地步。
去年,文学界经历了两次他认为可记入中国传统文学发展史的风暴打击:一是创刊于1981年的《文学报》停止纸质出版,二是创办于1993年的著名的《书城》杂志停刊——《文学报》风雨兼程40多年,在文坛影响力不言而喻;《书城》之前虽也经历过停刊复刊的反复,但引起的关注都没这次停刊巨大。
徐则臣很清楚,文化人对纸质阅读再抱有难以割舍的古典情怀,这个时代的阅读趋势、阅读方式和途径都已经发生了结构性的巨变——网络阅读和视听接受越来越成为日常阅读的新形态。“纸质阅读在当下已是极小众行为,很多人离开学校之后,可能再也不会拿起书本。”
徐则臣从不怀疑文学的价值,更相信小说不会消亡。这并不是小说家勉力要它“活”,而是人类对世界和他人命运的好奇不允许它“死”。但这一切首先需要让人知道——《人民文学》里就有这样的好作品。
在严峻的时代大势下接任《人民文学》主编,徐则臣必须在守成与变革间寻找支点,他将“运河式智慧”在文化传播领域实践,“运河从不会拒绝任何一条支流”,文学若固守象牙塔只恐加速枯竭。
进入直播间如同适度地打开文学江河上的水闸,将精英文学引入大众的原野。“平视文学的视角,或许更适合文学的土壤。”尤其在感受到董宇辉直播间这个“漕运码头”的文学带货能力之后,徐则臣更深切地意识到:“如果人们还习惯仰望文学,文学真的会被束之高阁。”
现在,他会要求编辑全流程作业,不仅要做上游的编辑事务,还要参与中游和下游的各种宣发、推广,要让作品从各个层面上被人看见。而文学影视化目前最容易被大众接受,那就不遗余力地去做。文化传播,需要的不是更高的堤坝,而是更智慧的河道。
徐则臣少时在运河沿岸目睹了故乡段运河因南水北调工程焕发新生,同时也伴随古村镇的拆迁,他对传统的消亡与重生有着切身的体会,放在当下的文化语境里亦然,“真正的传承不是博物馆化,而是像运河一样——古老的河床承载今天的流水。”


白色印花立领西装/Shiazy Chen
徐则臣的言行与文字极少偏激,始终带有一种“河道般的容纳力”。面对文化冲突,无论传统与现代,西方与东方,他都习惯于寻找共生的可能。
就如当下,他一方面在传播上推动精英文学大众化,因为“拒绝民船的官河,最后都成了遗址”,一方面在创作上扎根于严肃文学。“卖书可以,但不会把文学降格为鸡汤”。也正因为如此,他的一部《北上》写了四年。
这种精英创作与大众传播的二元统一,便是徐则臣“水系智慧”的一种体现。
他一时在甲板上吆喝卖货,一时藏身船舱里潜心创作。徐则臣在写作上一向自觉、清醒,善于规划。初入文坛,他以呈现地域文化的“花街”系列崭露头角,如同莫言的“高密东北乡”,苏童的“枫杨树乡”,获得鲁迅文学奖的短篇小说《如果大雪封门》属于这个系列;后来他书写命运沉浮的“北漂”系列,代表作是《跑步穿过中关村》;前两者结合起来则有了2014年探讨故乡与世界的关系、获得老舍文学奖的《耶路撒冷》;再后来他的写作更加宏大,有以北京城作为书写对象、探讨城市与个人的《王城如海》;再之后是《北上》,借助有着2500年历史的大运河“展示近百年以来的民族历史,使之成为审视中华民族发展的图谱、悠远的文脉乃至旧邦新命的一扇窗口”。这些作品中,或多或少都有着运河的影子。
“不同阶段有着不同的书写,主要是因为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问题和困惑,小说创作自然也会发生变化。”写作对于他而言,成为一种认知生活的方式。多年来,他之所以笔耕不辍,是因为他对世界一直好奇,而文学为他提供了找寻答案的有效路径。
30岁那年他开始写《耶路撒冷》,花了6年时间完成这部作品。小说围绕着一群70后的童年和中年,围绕着运河与花街,讲述到世界去又回故乡来的故事。这部小说从内容到形式,都称得上是“野心之作”。在过往很长一段时间里,处于夹缝中的70后作家境遇尴尬,跟50后、60后作家比口碑质量,跟80后、90后作家比市场销量,都比不上,“鄙视70后成为最保险的文学结论之一”。
而他打破了这个魔咒,《耶路撒冷》被称为“70后心灵史”,徐则臣也彻底浮出水面,被视为“70后作家”扛旗人。经历这场庞大、复杂的写作之后,从此他不惧触碰宏大的题材。
而无论题材是宏大还是厚重,是家国的还是历史的,他目光始终聚焦在普通人的生活、情感和选择上。他很清楚:相比养尊处优的上层人,讨生活的普通人更容易受到风吹草动的波及,他们的困境是大多数人共有的;而边缘人触及的生活面更多,负载的信息量更大,身上的故事也更多,更具典型性。
徐则臣北大硕士毕业后到《人民文学》当编辑时,最初没有编制,户口也不在北京,2012年才解决。他当了7年“北漂”,结识了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他把这些朋友写入小说中。他们从乡村走到大城市,“苦闷、彷徨、无助和坚持,以及摇摆不定地寻找”。对小说里那些办假证的、卖盗版光碟的、刷小广告的,他都视为朋友,看清他们,理解他们,甚至觉得“他们比很多文化人有意思一万倍”。他正视人性的复杂与弹性,读者也读到了他对生命的尊重和悲悯。
时光回溯到他的少年时期,在熙攘喧嚣的码头,他目睹了普通人在极端生存条件下迸发的生命韧性与人性微光,他说:“运河的伟大从不在宫殿里,而在扛包工人的脊背上。”


卡其色麂皮休闲西装、白色长裤/Tod’s
黑色衬衫、黑色皮鞋/Boss
徐则臣的作品中,常出现“行走在运河边”的人物,某种程度上也象征着他自身在时空夹缝中寻找身份认同。
回望过往,徐则臣总会笑着说,中国的每一个级别的行政区划,他都扎扎实实待过——小学在村里,初中在镇上,高中在县城,大一大二在地级市,大三大四在省城,研究生在首都。他笑称此番人生经历为“条条小路通罗马”。
他货真价实地靠读书改变了命运——人生的每一个转折点无一不是靠读书达成的;当作家的人生使命,也是在读书中豁然明确的;更重要的是,他没有走任何捷径,每一步都没有省略,每一步都竭尽全力。
写作训练其实从他高二就开始了,且称得上大剂量、高频次。旁人却不知,他是为了治病而开始写作——那时他患有非常严重的“神经衰弱”,他回忆:“晚上睡不着,白天精神不好,看书就头痛,整个人很绝望。”为了对抗抑郁,把内心的委屈、绝望、孤独释放出去,徐则臣每天都疯狂地写日记,想到什么写什么,写到哪里算哪里,不把自己写通透彻底了就没法学习。
这般天马行空、随心所欲、百无禁忌,以及与自己死磕到底的书写,持续到高中毕业,不但有效地治愈了他的抑郁症,也让他把自己写开了——表达力及想象力都格外自由。
要成为作家的念头,在大一暑假萌生。高考失利进入淮阴师范学院中文系,他为宣泄对自己的不满而拼命地泡图书馆。泡着泡着,心越来越静,几个月后,当他读到作家张炜的《家族》时,突然意识到:文学写作那么有魅力,当一个作家如此之好,可以把自己想说的都说出来,用一种更准确的方式。
自此,他确认了自己的人生使命,应了那句,“人生天地间,各自有禀赋。为一大事来,做一大事去。”
彼时,尚不清楚文学到底是怎么回事,那就把所有能接触到的文学书籍报刊都看起来,“小说、各种杂志都看,《世界文学》《外国文艺》,基本上所有文学杂志全过一遍,每期过。”
他尤其喜欢外国文学,找到了不少自己喜欢的作家。他看书从来都是逮着一个作家通读,把能找到的该作家的作品都看过,之后再看相关评论和研究。他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比如加西亚· 马尔克斯提到哪个人、哪本书,他会按图索骥地找个遍。就这样由点及面地编织自己的阅读版图,越织越密,越织越大。
他特别想看人称“穿裙子的马尔克斯”的智利作家伊萨贝尔· 阿连德的《幽灵之家》,在淮安怎么也找不到。此类事情经常发生,许多找不到的书他只能记在小本上以待来日。淮阴师范学院的藏书量远远不能满足他的阅读了,于是,当听说大三大四有到省城的南京师范大学的进修名额时,他毫不犹疑地报名,通过四轮选拔考试,最终如愿以偿获得全系唯一的名额。
南师大没有辜负他,徐则臣记在小本上的未读书目几乎在此都能找到。他整整两年都泡在图书馆里“穷凶极恶”地读书——从A到Z全部编目拉网式阅读,把整整一大间屋子的外国文学都看完了。一年精读的书籍有一百本左右。
那本求而不得的《幽灵之家》也终于在南师大图书馆查到,却一直被别人借着。他几乎每天都要去看是否归还,一连去了好几个星期才最终等到。
在这样广撒网的阅读中,徐则臣把文学的脉络梳理出来,建立了文学的整体观。同时,他也在南师大留下了“传说”——图书馆在山包上,宿舍在山下,于是,每天都能看到一个人,像傻子一样抱一摞书,今天抱上去再抱下来,明天抱下来再抱上去。
大学毕业回淮阴师范学院当了两年大学老师之后,徐则臣认为自己依然不能像个正儿八经的作家那样写好小说,于是报考了北大中文系,师从曹文轩。研究生毕业,应聘到《人民文学》杂志做编辑,再到今日的主编。
而细究这一条条励志的“小路”,发现其背后也是一条条“水路”:他出生在多水的江苏连云港之下的一个小乡村,初中就读的学校门前是石安运河;之后在江苏淮安读大学,此地在明清时期就有“运河重镇” 之美誉;后求学、生活于北京,又是京杭大运河的终点。从南到北,从小村到都市,从运河这头到那头。
他的人生随运河流转,精神血脉亦因之丰盈:在淮安读大学时,他常独自考察明清漕运遗址,触摸石闸上的刻痕,沉淀心性“与历史对坐”;初到北京受挫,他沿着运河行走20公里,看见河水裹着垃圾流淌,他明白了一件事:肮脏不是停滞的理由;作品获奖享受荣光,他走过运河上的老石桥,“桥洞下打盹的流浪汉提醒我:文学若离开地面,就会和断流的河道一样死去。”
在《北上》的写作中,徐则臣日益发觉:一个写作者,终究要与根植于历史土壤的文学传统对接。《北上》动笔之前,他读了六七十本书,看了几十部纪录片,中国著名的河道几乎走了个遍。他尝试把史诗融入小说主人公的生命历程中,“使之有效契合,互为因果”。这让他进一步意识到,想要写出真正的中国式小说,就必须要了解中国民间文学和传统文学,这方面他需要补课——青年时候,他痴迷外国文学,这一条条丰沛的“精神支流”为他提供了丰富的滋养;人到中年,血脉觉醒,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前所未有的热情。为此,他考上了莫言的博士。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显然对中国本土文学有卓有成效的理解和强有力的发言权。徐则臣寻求的,是更深度地回归和融入中国传统文学这条浩瀚的主流。
从个人探寻,到文学求索,徐则臣都蹚出了一条独特的“水路”。


深灰色夹克、银灰色衬衫/Giorgio Armani
墨水笔/Montblanc艺术大师系列致敬雷诺阿
横格笔记本/Montblanc
一流文学被影视改编后
窄化是必然
Q
您写了20多年的运河,现在以大运河为写作主题的《北上》更是广为人知,有人说您是“运河之子”。
这个名头太大了。我是对运河有感情,把它作为小说故事的背景用了很多年,我已经欠它很多,也该让它从后台走到前台做主角了。它不仅是一条河流,还跟中国2500年的政治、经济、文化密切相关。我希望人们能够真正认识这条流在大地上、历史教科书里,以及中国人血脉里的河流。除了写它之外,我也做不了更多的事情。
Q
《北上》电视剧的改编,很多原著党表示不能理解,您自己怎么看?版权卖出去以后,我不参与也不介入改编。现在的改编,我其实没啥意见。因为电视剧这种艺术形式的特点,如果完全按照小说去拍摄,可能会没人看。
把小说如实改成电影、话剧都没有问题,因为大家坐在那几个小时不动,故事情节再跳跃再蒙太奇都可以;但电视剧一天两集,今天播的跟昨天的如果割裂,观众就不会看;看电视剧时,人们一般还干点儿别的,一抬头发现看不懂,可能很快就会换频道。
Q
可有读者遗憾,小说里明明已经创造出那么成熟精彩的故事,为何电视剧要另起炉灶新写一个书中几乎没涉及的年代?
目前大家可以看到《北上》改编的三个剧,话剧、音乐剧和电视剧,每种剧都有自己的侧重,音乐剧选的是1901年的时间线,话剧比较贴合原著“古今交织”的叙事,电视剧侧重的是当下。要是单独看一个剧,可能就不太接受,但是几个剧放在一起看,就知道他们与自身的艺术规律和市场要求是契合的。三种不同的艺术形式可以相互印证,拓展原著的宽度和深度。不同的艺术方式,选择的点,建立的逻辑,是不一样的。都看看,能够更好地融会贯通。
Q
有一种说法,一流的文学作品很难改编出一流的影视作品,反而二三流的小说,经常会被改编得很好。
这很正常。一流的作品里面负载的信息量很大,无论是艺术、故事、思想,还是社会信息量……改编只能选取其中的一些面向,毫无疑问一定是窄化它的。指望一部优秀文学的影视改编超过作品本身,可能性很小。而二流三流的作品,可能某个点到了,却没有拓展好。好的导演、编剧、演员就有充分的空间进行二度创作,一起在那些需要拓展的地方用足力,影视剧反而好看了。
从故乡到世界
不是单行道
Q
写作30年,您的写作有什么流变?
大部分人在写作上都是从艺术起步的。艺术是什么?艺术是一种感觉,一种审美触动,比如,“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比如,白墙黛瓦,烟雨江南……
写着写着,发现老是写这些外在的、自足的或漂亮的东西,不过瘾,开始有了问题意识,开始关注日常生活。生活琐碎,不具有那么高的审美品质,如果没有一个问题把它们串连、激活,就是零散的一地鸡毛。等到艺术能力足够,会发现一地鸡毛也可以作为审美的素材和处理对象,你就会慢慢地对日常生活感兴趣,开始写现实,因为打开门扑面而来的就是现实问题。
我生活在北京,所以我要处理北京的题材。人到了中年会回头看——这是人基因里的东西,你会考虑“你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会看来路,所以一定程度上会处理历史——个人的或家国的历史。所以那个时候我才会开始写《耶路撒冷》,写《王城如海》,写《北上》。
Q
您的作品非常多,《北上》之外,您会推荐哪些?
如果向年轻人推荐,我推荐《跑步穿过中关村》。这个小说有一定的时代性,却也有超越时代性的东西,就是一群年轻人如何去解决人和城市之间的关系。
它是我目前为止被翻译最多语种的作品,大概二十种语言。国外读者尤其感兴趣,他们想看到中国一代年轻人的状态。
Q
《耶路撒冷》讲故乡和世界的关系。在我小的时候,觉得世界跟故乡是二元对立的,想要走出去;人到中年,我发现故乡也有可能是世界,两者之间能够互通。过去我以为从故乡到世界是个单行道,但现在我认为它们是双向的。
这是一部中年之书,一个青年人进入中年以后会体会到很多东西。在这本书里,我基本上把我认为一个青年进入中年的精神、心理、思想等状态,比较充分地表达出来了。
Q
您还做了很多事情,比如经常回到淮阴师范学院,设立奖学金,给师弟师妹们讲座授课,有时候不仅仅自己回,还带着作家朋友们一块儿去,是想撒播文学的种子?
我是发自内心想要做这些事情。当年我在师院做学生,想见一个 “活”的作家,近距离地接触,非常难。现在这帮孩子其实就是当年的我,当年我需要的我想他们应该也需要。事实上的确如此,所以我每年都带作家过去。多大情怀谈不上,就是觉得孩子们不容易,我恰好能给他们提供一些资源,且对我来说,只是举手之劳。
Q
在各种采访时,您从不避讳说出自己不算高的起点,对自己的来时路坦诚实在得令人惊讶。
作家写作某种程度上就是一种自我袒露、自我剖析,是对自己的诚实,也是对读者的真诚。
写作上我坚持“修辞立其诚”,工作上我也以“诚”贯之——既真诚又诚实,还诚惶诚恐。我一直在做文学编辑这件事,如果尸位素餐,我会心虚,所以我一直认认真真,问心无愧。
Q
最近略萨去世,您在散文自选集《一意孤行》里提到中国作家应该学习拉美作家写出“真正具有民族气质但又能抵达整个世界的作品”。
那天略萨去世了,我说一个作家想过的生活,略萨全部过了。略萨本人及其作品几乎走遍了全世界。文学一定是要走向世界的。文学创作的最终目的是什么?交流!不是孤芳自赏,是要最大限度地交流。作家写出作品就希望更多人知道,能够与更多人产生共鸣,得到呼应,增进理解。
前些年我出国比较多,到大学,去书展,参加出版社组织的活动,跑了接近30个国家,更加深刻地意识到,作家应该是世界公民,要尽可能去感受全人类的情感,去体察全人类的经验。
编辑-颜语
新媒体编辑-锦鲤
撰文-林中歌、源木
摄影-谷子@谷仓摄影
形象-焦淼
化妆、发型-雪薇
服装统筹-Amy


这是一条公告